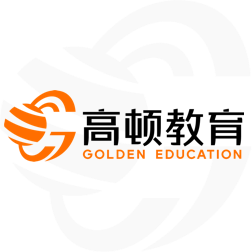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只是*9步。我们都明白权力的本性,它困在逼仄的笼中,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呢?恐怕时时刻刻,它都企图冲破桎梏,放纵爪牙。法治这一道锁链,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它身上再加一道锁。法治是外在的限制,这一道锁,则侧重于内在的限制。
此即分权,顾名思义,即把笼中的权力大卸八块。这八块,不仅要接受法治的约束,还要相互制衡。
为什么要分权?此中道理想必不难理解。这就像,假如只有一个人,他得自食其力;两个人,便有了竞争的利害;三个人,勾心斗角必定加剧。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虽是反面的案例,却充分印证了制衡之理。
当然,现实之中,常见反例。今日中国,我们将司法权一分为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各得其一,本希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三国之魏蜀吴,互相制约,不曾想在一些地方却沦为了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一心对外。这证伪了分权吗?不,这充其量只能说明,错误的分权,效果会适得其反。甚至,这压根就不是分权,而是分职。分权是将权力分在了三到五个碗中,各碗之间相互独立;分职只是将权力分成三到五份,不过还在一个碗中。
关于分权的必要性,现代分权学说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早有精辟论述:“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担心这同一个君主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推行。”“司法权如果与立法权合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就将由专断的权力处置,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司法权如果与行政权合并,法官就将拥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由同一个人,或由权贵、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构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国家决议的权力以及裁决罪行或个人争端的权力,那就一切都完了。”
三权分立的典范,非美国莫属,以至我们一说“分权”,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美国,而非它的发源地英国。美国的分权,几乎将制衡做到了极致,这三权,一面独立自主,另一面环环相扣。我们都艳羡美国的司法独立,然而其司法权的独立,并不等于是独立王国,它依然要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衡。这尤其表现为法官的选拔。如美国联邦*6法院的九位大法官,被尊为圣人,介于人神之间,他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一是总统提名,二是参议院同意,换言之,行政权与立法权都有机会杯葛大法官的诞生,尤其是参议院这一关,曾阻断了罗伯特·博克等法界名流通往美国联邦*6法院的圣殿之路。反过来,待大法官被任命,他就完全独立,甚至常常反噬提名他的总统。由此可见,立法权与行政权制衡司法权,司法权回过头来再制衡立法权与行政权,三权相爱相杀,目的只有一个:保障公民权利。
话说回来,分权是定理,三权分立却非定理。换言之,宪政国家,必须要分权,至于怎么分,分成几块,当取决于传统与国情。孙中山先生痛感三权分立之不足,创制了五权分立,成就了与“三民主义”齐名的“五权宪法”。他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这二权,皆源于中国传统,譬如监察制度,在古代中国的行政体系当中,所发挥的效用非同一般,当然,说到底,它只是皇权的一个枝节,依附而不独立。孙先生的五权说,正试图使其独立出来,以监督其他权力,这大抵可谓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惜,无论孙先生生前还是身后,包括现在的中国台湾,五权宪法的现状,仍远远落后于理想。“驾乎欧美之上”的立意,目前来看,还是一轮幻影。
是不是权力分得越细越好呢?自然不是。我们除了追求公权力之间的制衡,还要追求其工作效率。“小政府”固然是我们所愿,然而政府的权力小到连一个杀人的凶徒都缉拿不了,连一个公共图书馆都建造不了,显然违背了我们依社会契约建立政府的初衷。所以孟德斯鸠将权力一分为三,而非更多,正有其深意存焉:为了兼顾制衡与效率。有些国家,觉得三权分立有损行政效率,干脆简化为两权分立,如让立法权与行政权穿同一条裤腿,另一条裤腿留给了司法权,以为制衡。更有学者依此——权力结构的重心——将宪政国家分作了立法国家(如英国)、司法国家(如美国)与行政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
不论是两权分立、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不论是立法国家、司法国家还是行政国家,分权,正如杰弗逊对约翰·亚当斯所言:是一个好政府的*9原则。反之,“把全部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集中,不论交给一个人、少数人还是许多人,不论实行世袭制、自我任命制还是选举制,都可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暴政”。


 QQ登录
QQ登录 微博登录
微博登录 微信登录
微信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