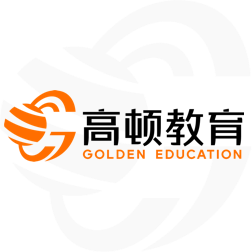近日,北大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法学院新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该院教授龚刃韧在文中称,按照新政策,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人员。他认为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及“核心刊物”毫无关系。贺卫方、汪建成等教授都发文赞成龚的意见,认为这种涉及教师重大利益的事不能院领导研究就定了,应征求老师们的意见。(《新京报》2月4日)
北大无小事,涉及工资分配之类改革的就更不是小事了。张维迎几年前主持的北大改革所激起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在官本位和行政化气味浓厚的大学体制下,领导班子不跟教师商量而独断地推出个考评条例、分配方案什么的,在其他大学往往很“正常”,但发生在北大法学院就格外让人感觉不正常了。一来北大有教授治校的传统,二来以追求正义为己任的法学共同体在自身事务的治理上更首先践履正义理念。整天跟学生讲程序正义,学院却把程序正义踩在脚下,这种分裂会给学生怎样恶劣的暗示?连北大法学院都这么干,可见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已严重到什么程度。
众教授不满领导独断的新政策对教师利益的损害,以“邮件群讨论”这种半公开方式表达批评和抗议,这符合北大传统——你不民主,我以这种诉诸公共讨论的方式逼着你民主。当自己切身利益受到权力侵害时,不是姑息纵容和消极忍受,而是积极地站出来高调地扞卫自身利益,毫不留情地抨击,这样的教授值得尊敬。不过,我更尊重这样的教授,他们不仅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才站出来,不仅是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才拍案而起,面对那些看起来与他们利益无关的不公和丑陋时,他们同样会站出来大声疾呼。
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很可贵;为那些表面看起来与自己无关的权利而斗争,因为超越了利己本能而更加可贵。
在北大法学院诸教授奋起抨击本院领导专断之际陈述上述道理,绝非暗讽诸教授在只有涉及自身利益时才奋起维权,而是想吁请其他高校的教授们也站出来抨击大学中这种愈演愈烈、肆无忌惮的官僚习气,而不是只有当事者北大法学教授们的孤身奋战。行政官僚习气对大学的浸染根深蒂固,不是几个教授可以撼动的,也不是个案可以消弭的,它需要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努力,需要教授们联合起来反抗行政权力的指手划脚,合力驱除官气以争取大学自治。不要事不关已就谨守沉默是金,不能只有损害到切身利益时才选择开口。这方面,近来上书敦促修订拆迁条例的北大五教授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自家的房子并未有迫近的强拆威胁,但他们一样站出来了。
不要以为行政化问题与你无关,也不要以为消极退让就可以躲避官僚独断之害。肆无忌惮的权力,总有一天会将它的铁骑踏入你权利的领地。你不关注问题,问题会找上你。你对问题退避三舍,问题会得寸进尺。
可惜在反抗大学行政化上,知识精英们缺乏这种共同的利益感觉,于是就很少见到共同的权利行动。近年来教授反对官僚专断的事件发生了不少,不过都停留于切身利益受害者的孤身作战上,虽有舆论声援,但常常缺少最有力的、来自学术共同体且诉诸实际行动的力挺。直接受害者孤立无援,其他高校的同行大多保持沉默。典型如几年前的人大“张鸣事件”,张鸣教授一个人冲在前头口诛笔伐,少有高校同行站出来一齐向行政化开炮。他们也许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地隐忍,这样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正如很少有人会想到,甚至连北大法学院这样本该尊重教授自治的地方,都受到了行政化和官本位的侵染。
大学,本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中地。“公共”之意,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称“公共”,就是能突破对一己之私利的关注,而把自己关怀的视野扩展到那些与个人利益表面没有关系、却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上。可大学和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公共性都日益式微了,知识精英只关注自己门前的那一亩三分地,无关自己切身利益就不会站出来。只要官僚化尚未直接伤害到自己,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绩效工资,就可以置身事外地做一个看客。大学行政化日益严重,与教授们对官僚专断的集体绥靖不无关系。
当然,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在无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站出来,甚至能拒绝不正当、不首先利益的诱惑而扞卫规则的正义时,那就更可贵了——可惜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人,我从北大法学院官方网站上查看到该院领导们的身份,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我想,当这些学者还不是院领导之前,一定也非常厌恶学校和学院中这种官僚专断之风。然而当他们当了领导之后,立刻就染上了官僚习气,走向了反民主之路,没有抵制住权力专断之诱惑。学者向官僚的轻易蜕变,也是此事非常可悲之处。


 QQ登录
QQ登录 微博登录
微博登录 微信登录
微信登录